|
写在前面先亮个评价。对于我个人来说,这部片不但是这个清明档最好的电影。也是绝对稳居今年华语十佳的一部片子,而且有很大概率是我的前三。这点我希望所有人都去看,但也恐惧所有人都去看。《第十一回》恐惧的原因很简单,这部片在前期宣传上一直被当做商业喜剧,但它内容上其实离商业性相去甚远。昨天上映后,大量没弄明白的普通观众涌入,最后的结果就是豆瓣评分跳水,从上映前主要以影迷打分为主的8.5,到上映一天后的7.5,落了一分,落得我都有点心痛。包括昨晚后台留言也有很多人直接说,觉得《第十一回》是烂片,看不懂等等。所以写这篇文的目的之一,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调整好预期,这不是一部有周迅,有大鹏,有陈建斌的商业喜剧,而是一部需要极高的观影门槛,充满大量留白和隐喻的文艺片。值得看,但也要好好花心思,动脑子看。(以下有剧透,不剧透这片没法写)一马福礼A和马福礼B聊《第十一回》需要先明确一件事,就是不能够只用我们平时熟悉的那种直叙视角去打量它。这是一部需要代入核心概念,再去倒推,观赏,才能品出多重味道的电影。这么听起来还是很玄乎,但其实很好理解,我先把故事一说就明白了:电影讲述的是以曾因面子而认罪坐牢的杀人案当事人马福礼(陈建斌饰),因案件被市话剧团拿去改编,不满自己被广泛传播为杀人犯,重新走上了自证清白之路。有趣的是,解读这部电影的方法,是在这个过程中,通过角色的台词告诉观众的——于谦扮演的话剧团团长傅库司,跟一直自认满腹冤屈的马福礼这样解释:“生活里的是马福礼A,舞台上的已经是马福礼B,你不要把他当做你。”什么意思呢?他说的不仅仅是一体两面,而是在生活中时常出现,关于身份与名字的黑色错差。就拿马福礼来说,在生活中卖早点,坚称自己没有杀人的他是A。而作为案件当事人被搬上了舞台,代表了不踩刹车,因为妻子和外人偷情而蓄意谋杀的杀人犯的,是B。那当马福礼这个名字出现在作家笔下的书、被百姓当作谈资,或者就像现在这样,被拍成了电影的时候,会出现什么情况?自然就是无穷无尽的马福礼C、D、E、F...了。这种AB你可以代入任何一个名人的身上,名字还是那个名字,人还是那个人,但经过层层加工,涂抹之后,哪个才是真的?哪个才能代表原始的马福礼?以这种不断颠覆,解构的思路代入到《第十一回》中去,你就会很快品味出它的好玩和多义。导演将这种AB概念用类比,比喻,化用到了全片之中。最明显的肯定是主线这个历史疑案本身——一开始的版本是话剧团自己理解的,马福礼因为妻子和外人偷情,松开刹车而蓄意谋杀而后马福礼不满,自述并非有意,是刹车失灵之过,当时只是为了绿帽子尊严才承认杀人。借着当年男方被杀者的富商亲戚登场,让舞台上出现了又第三版,是马福礼老婆勾引的男小三。最后是官员上来,怒斥伤风败俗,要求必须按照官方记录在案的“历史”来重写剧本。第四版出现。这些版本里,又诞生了ABCD4个不同的马福礼,电影会引导你去好奇,哪个是真,哪个是假?然后在电影最后狠狠给你一个嘴巴子——因为ABCD都不是真的,反而是通过马妻的远方表姐口中的话拼凑出了一个真相:没有什么男小三,也没有杀人犯,那是马福礼妻子的初恋情人,被家长强制分开,再无缘分,心如死灰,所以故意把刹车弄坏,在车底刻好了一张和情人的结婚证,让情人与自己一边在车底做爱,一边一起死去,完成了这桩单方面的浪漫殉情。“我就要在人生最后一刻,跟你融为一体地死去”可这就是真相了吗?表姐的话里又有没有虚构的部分呢?这是春夏那个角色在舞台剧里主导着演出来的,是不是也存在可能,因为她本身的对马福礼妻子的共情,而美化了一切呢?真相不重要,且无解,认清这不一定是真相,有所怀疑,才更重要。编剧还用了两个特别妙的意象,去把这种表达铺排进电影的很多角落。一个是豆花。马福礼在自证清白的道路上一直摇摆和游移,只能拎着豆花去求问别人的看法。鼓励马福礼去证明真相、取回清白的律师那里,他抱怨豆花太咸。而力求逝者安息,劝马福礼放下的大舅子那里,豆花是“根本没放盐”的淡。同一碗豆花,到底是咸了还是淡了?马福礼还更详细地追问了一句:“如果豆花是咸的,那是盐放多了,还是豆花少了?”你看,同一碗豆花,就能被吃出4种“观点”。这看似只是基于食物口味的追问,实际是以小比大,类比我们生活中具备哲学意味的难题。这里的豆花,在电影里指代的就是始终无法被明确定义的案件真相。而电影之外,豆花味道的比喻,指的就是对同一事物,会有不同目光的打量。另一个是苹果。有一段是贾梅怡(春夏饰)在化妆间正拿着一只苹果把玩,一个演员推门进来问“我的苹果呢”并开始寻找,蓄意制造一种此苹果为彼苹果的错觉。但随即观众就能明白,演员真正找的是“苹果手机”。这里的苹果,象征的是局部。苹果是吃的还是用的你怎么看?你看见的,究竟是真的,还是只是一部分的真?没有答案,这些问题都不需要答案,但需要被一直问,一直问。二冒犯与温柔整个《第十一回》都带着一种,我很难在其他华语片中的气质。这种气质和导演陈建斌这个人倒是还挺统一,都是一种表面糙,冒犯,解构,批判,但内里却是写着小诗的温柔浪漫。我们就两种都聊聊。里面的故事对所有人物都是带着冒犯性的,所有的笑点呈现都是通过给观众“看傻逼”的方式。律师是满口正义,满口追求真相却从不帮人的假斗士。富商是信佛,但挂着耶稣像,拿钱买路的假善人。艺术家是每天掉书袋,喊叫艺术至上,背地里却出轨和女演员乱搞的伪君子。私人诊所的医生是口头医者仁心,但见了红包就立刻收进的伪仁者。俩主角也逃不过。马福礼和金财铃夫妇都属于那种愚昧,死要面子的底层小人物,为了掩盖家里女儿意外怀孕的事情,假装自己怀孕。最后解决话剧问题靠的还是金财铃假怀孕,去碰瓷撒泼,才让话剧团停了演出。但是陈建斌把这些人处理得又特别温柔可爱,让你怎么也讨厌不起来。 电影实际对“人”是一直有所关怀的。它希望剖解各阶层人物的无知,私心,与暗面,也甘于展示他们幽微的真情,温暖,与柔软。 马福礼听到多多说了那句“不想要一个杀人犯爸爸”后,因为始终无法自证清白,想到了一个办法,就是去弄一张死亡证明,以失去身份的方式提供给孩子安全感。 这个方法实在很笨拙,可也很诚挚,至少当我看到已经备受劳碌的他,掏出那张纸的时候,我觉得他无限贴近一个好父亲的样子。 最具体的还体现在了金财铃和多多这对母女的塑造上。 在多多决意打完胎,也用假肚子来让家人放心时,金财铃通过女儿掩饰苍白的口红色,以及她的裙子迅速明白了,并通过捡筷子,在女儿肚子上验证了这一点。 而金财铃没有选择戳破。 就在那个瞬间,母亲和女儿的心意实现了微小的共通,这是她们共有的秘密,是她们对彼此达成的体恤,更是不曾言说,但也不曾终止的一份相互的爱。 也是因为这个瞬间,金财铃强硬之下的柔软得到了披露,多多疏离外表下的释然与决绝,也预示着一次向阳的成长。 她们都有各自的苦,也都体认着彼此连绵不断的羁绊。 包括贾梅怡这个被胡昆汀一再哄骗的文艺女孩角色,除了纯真之外,她又是清醒的。 她虽然受惑于胡昆汀的艺术理论魅力,把自己一再代入到杀人案中那个悲苦而深情的赵凤霞,但最后话剧上演,章节里那句“梅怡痛吻胡昆汀”已说明了一切。 她对关系的醒悟与斩断,对艺术的执着追寻,都是无声又饱含力量的。 从这些人身上,我们都很难去提炼出一些绝对的正面或负面的形容词。 可也正是因此,电影体现出了人的复杂与形色,以及很难得的,感受到了他们遍布市井,遍布四周的可信与真实。 我最喜欢的一段是电影的结尾,马福礼和金财铃坐在颠簸的马车上对谈。 马福礼不知道多多已打胎,幻想构思着“小马”的新生与未来,而知情的金财铃依然没有戳破,她聆听着丈夫的雀跃,如同聆听一段最美好的图景。 一切尚有希望。 这份知情的藏匿,对不知情的欢欣的包容,正是电影所蕴藏的,对于难以言说的爱,对于难以言说的人,始终抱有的温柔底色。 三被指手画脚的艺术这一段本身应该是被放在冒犯里面的,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单独拿出来聊一聊。因为这段冒犯太有趣,也太辛辣了。我们现在试试抛开电影整个故事,花里胡哨的叙事结构,上面我们写的所有情感游丝,就单看戏剧本身的遭遇,其实就能很明白地感觉到导演到底在冒犯什么了。胡昆汀排的这出戏,被叫停了5次。第一次是因为“杀人”的当事人不满。第二次是因为“被杀”的富商亲戚不满。第三次是老一辈的同志不满。第四次是审查的官员不满,要求重写剧本。第五次是对导演私德的指控而波及戏剧。那么思考题来了:胡昆汀喊出“这出戏没法排了!”的时候,谁导致的这出戏的死亡?什么在入侵艺术,电影没有明确告诉你,但“灵魂强奸犯”和“乌龟王八蛋”这两个词不断出现又好像在控诉些什么。看着这问题我知道你们在代入什么,我也在代入同样的东西。但我们好像都无法说出来。历史真的成了一位任人打扮的姑娘,谁都可以过来给她脸上涂一遍,然后叉着腰挺着肚子说,历史明明是这样的!你们这么拍是歪曲历史。有人靠闹,有人靠钱,有人靠道德纠察,有人靠权。有人代表庸众,有人代表富人,有人代表道德家,有人代表权势。闹没有钱好用,滥用道德会被反噬,喝完大酒要写检查,最后还是靠权压倒了一切。这是什么啊,这他妈《大佛普拉斯》啊。在这个角度上,好像比来比去,只有大鹏那角色是真的爱这场戏剧的人。虽然这个角色虚伪,掉书袋,有着很多艺术工作者的臭毛病,但他的爱不是假的。所以他才可以放弃导演署名,放弃名誉,哪怕被改得七零八碎,也要让这出戏上映。但戏剧依旧免不了是浮萍式的命运,艺术像是四面楚歌的霸王,抱着缪斯化的虞姬春夏,被碾来碾去。历史啊历史,真相啊真相,那啥啊那啥。演员不能说那啥,所以只能用一块红布隔绝那啥。什么是这出戏的历史真相?你真的知道吗?不要嚣张地叫唤你的知情和笃定,唯一可信的只有那台沉默的拖拉机。而它,没有刹车。配图/《第十一回》音乐/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ibhjw.com/kjsczz/13739.html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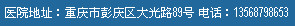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