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作者 黄扯扯 十点人物志原创 “有一个你不想要的孩子,是什么感觉?”国外社交网站Reddit上,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万多条回答,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唏嘘。但在知乎上,同样的问题,只有39个回答,几乎都是匿名。张洁是唯一一个亮出身份的答主。刷到这个冷门问题的时候,她像对着树洞一样把亲身经历一吐为快。不到12个小时,阅读量破了9万,获赞数超过;一周后,涨到了36万,点赞。底下的留言里,人们纷纷表示理解:“太多鸡汤文让父母要无条件爱孩子了,可是爱都是要相互的啊。”那个“不想要的孩子”,是自闭症。确诊 公交车开出去不到一站地,怀里的孩子又开始哭了。尽管是非高峰期,车里人也不少,有人看到张洁抱着孩子,起身给她让座。她刚坐下,儿子就嚎啕大哭。她小声哄着:“星星不哭,很快就到了。”没有用。星星听不懂她的话,自顾哭着,嗓门洪亮,伴随着身体左右扭动,想要挣脱妈妈的怀抱。半个公交车的人都投来不解的目光,“怎么回事,孩子哪里不舒服吗?”刚刚让座的好心人问。张洁感到无地自容:“他是自闭症······”说话间车停了,这不是她的目的地,但她带着星星下了车。她毫不怀疑,如果不下车,星星能嚎一路。刚下车,后面来了一辆6路,星星立马不哭了,拉着张洁的手要上去。6医院,张洁叹了声气。最近,张洁天天带着星星往返于家和这所与北医医院之间。从此以后,只要是坐公交,不管去哪里,星星必须坐6路;如果强行带上别的车,就大哭大闹。这是自闭症的典型症状——刻板行为。星星18个月,还不会说话,张洁叫他也没反应。起初她以为是听力问题,但儿子明显能听见声音,就是不理她。正对他的时候,他眼神飘来飘去,从不看她。最让她担心的是吃饭。同龄孩子都长出牙齿,已经可以吃蛋糕、水果。星星也长牙了,但任她怎么示范,星星都不会咀嚼,只能吃糊糊。母亲的直觉告诉她,孩子有问题,家人却说她敏感。她上网查,发现这些是自闭症的早期症状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后来,她不顾家人反对,医院排了一夜的号,抱着星星去看自闭症专家门诊。诊室的门是粉色的,里面也刷成了粉粉嫩嫩的颜色,但在这间色调温暖的房间里,她的心掉进了冰窟窿。专家看了不到五分钟,就让张洁去做评估。张洁之前跟别的家长打听过,“评估”就意味着确诊。据统计,在中国,有超过万的自闭症患者,其中七成有智力障碍。这与公众印象之间存在巨大偏差,很多人以为自闭症是性格不合群,是心理疾病。但专家告诉张洁,自闭症是一种大脑发育障碍,是世界范围内的医学难题,至今没有治愈的先例。有的患儿直到成年以后,生活都不能自理,需要父母24小时贴身照顾。医院的六楼专家诊室,张洁差点当场从窗边跳下去。干预 自闭症虽然没法治,但有大量的研究表明,可以通过干预改善患儿的行为。而专家告诉张洁,干预的黄金期非常短,要赶在孩子5岁之前,越早越好。张洁一度暗自庆幸,她发现得这样早,干预及时的话,星星应该很快就和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。那时,专家说了一句话:“发现得越早,意味着越严重。”她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两年半以后,我在南京资历最老、资质最完善的干预机构里,见到了张洁母子俩。星星在上辅导课,三个孩子围坐在一张方桌旁,桌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玩具,老师的职责就是教会他们如何玩。自闭症患儿因为理解能力和想象力的欠缺,普遍不会玩。一大堆玩具摆在他们面前,他们只会拿起最简单的一件,反复摆弄。其他的,不是因为不喜欢,而是不会。有个和星星同龄的男孩,已经会用塑料棒拼数字了。他在桌子上摆出一个“”,老师问:“这是什么?”他清晰地回答:“一百七十五。”张洁看着他,眼神复杂。星星已经干预了两年半,进步缓慢,一个扔球、接球的游戏,他学了半年;一年以后,才学会鹦鹉学舌,而且不超过两个字。像男孩这样和老师一问一答的互动,他几乎做不到。更多的时候,张洁问他:“我是谁?”星星重复:“是谁?”她又说:“叫妈妈。”“妈妈。”她有时会沮丧地想,可能儿子这辈子也不会理解“妈妈”是什么意思,不会真正地喊她一声“妈妈”。时间花了,钱也花了。干预机构的学费贵得吓人,半天的常规课程,一个月要;辅导课属于另外加课,一个月;如果找老师加做一对一的干预,按小时收费,到不等。张洁每个月付给机构的钱,将近2万,却收效甚微。这两年她胖了很多,她1米72,原来斤,有一张标致的瓜子脸;现在胖到了,尖下巴变成了双下巴,育儿焦虑写在了她的脸上。身体上她也吃不消了。带自闭症孩子上课不比得普通孩子,疲惫程度翻倍。带星星上常规课的时候,除了一对一的个训课,张洁可以稍微踹口气,其他两门都是对她体力和忍耐的极限挑战。小组课,5个孩子一起上,老师教音乐、绘本或手工,需要家长配合。星星根本坐不住,满教室跑,张洁在后面追,刚把他按回座位,一个没留神又跑了。感统课更是张洁的噩梦,一个大教室,30多个孩子一起,只有3个老师指导,张洁不得不追、哄、骂轮着来。在“物理攻击”之外,更残酷的是精神打击。手工课上,比星星晚入机构的孩子都会跟着老师做了,星星还是一脸茫然,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。张洁当初“一年后就会讲话,三岁就好了”的信心,崩塌了。老师安慰她,“星星的程度比较严重。”程度,是机构里经常使用的词语,在相同的干预下,它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孩子可以达到的天花板。实际上,星星的自闭症属于重度低功能,是最没有希望的那种。她整个人就跟崩溃了一样,“在家里疯了闹了笑了”。她甚至想过离家出走,不管孩子,她跟丈夫闹过不止一次离婚:“你放过我,我净身出户,把孩子给你。”接受张洁的人生,曾是全然不同的基调。她出生在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,父亲是大学教授,她从小耳濡目染,是人们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她身上有很多标签,概括为一个词,就是“优秀”:本硕,博士,大学老师,31岁上副教授,往后是教研室主任、系副主任,平步青云。她是那种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做到的人。喜欢骑车,学校离家10公里,她每天骑车上下班。后来骑行进藏,别人当作不得了的大事来说,她的语气就跟“去一趟(南京)新街口差不多”。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推进,包括生孩子,她和丈夫也是等到经济条件成熟以后才考虑。星星确诊后,张洁曾无数次复盘自己怀孕和生产的每个环节,她想找出原因,如果当初自己做得更好一点,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出生。然而没有。怀孕期间,他们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,孕检、唐氏筛查,这些都查不出自闭症。张洁本人冷静克制,她跟丈夫说,如果出现先兆流产,一定不保胎,“那是大自然在淘汰不合格的生命”。他们对自身也很严格,烟酒不沾,张洁在学校有独立办公室,连二手烟都避开。张洁想不通是哪个环节出了错,专家说,自闭症是天生的,就像上帝掷骰子的随机事件。说直白点,这就是命。以张洁的性格,肯定是不认命的,她一向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。机构里,成功的例子也不是没有,比如哪位妈妈,辞职带娃,机构、家庭干预两手抓;甚至生二胎的前一天,还要亲自带大宝上课,孩子进步突飞猛进。“劳模妈妈”的故事激励了她。她跟学校请了一学期的假,在家自学干预,机构没课的时候,她就手把手教星星。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专业书,《孤独症早期干预丹佛模式》《自闭症儿童社交游戏训练》,她买了一大堆,每一本都认真做了笔记,她感觉自己懂了,但实操过程中,星星完全不配合,注意力涣散,眼神对视不超过十秒。她气得扇过儿子耳光,扇完内心充满了挫败感。“以前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努力做不到的,哪怕是我最不擅长的论文,憋呀憋呀总能憋出来。”儿子让她四十多年的世界观动摇了,她开始怀疑,资质和努力,到底哪个更重要?她曾经坚信,自己前半生取得的成就都是靠努力得来的;现在,她发现不过是自己运气好,父母给了她不低的智商、良好的成长环境,家里亲戚大都是高校教师,上学时遇到的导师人脉好、资源好······在反复的挫败和绝望中,张洁心里冒出了“恶毒”的念头。有一天,她忍不住跟另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说:“我有时会幻想这孩子意外死了。”对方回应:“我也想过,很可怕,人真的有时很魔鬼。”第一次见到平素强大的妻子如此崩溃,张洁的丈夫很震惊。和张洁不同,丈夫面对儿子得了自闭症这件事,有一种平静的钝感。张洁又哭又闹:“星星一辈子都是个傻子。”丈夫安慰她:“多大事啊,就养着呗,以后有咱们一口吃的,就有他一口。”接受了星星是个“傻子”,张洁变得“自暴自弃”起来。一个指令教不会,那就不会吧,她也不再逼星星,“就好像一个学习很用功的小孩,无论他怎么用功,学习还是上不去,他就慢慢算了。”松弛下来后,张洁发现了星星身上的闪光点——容易快乐。周末的时候,她和丈夫带星星去公园骑车,星星特别开心,骑得飞快,两个大人都追不上。丈夫拴了根绳子在车把上,在后面拉着,“跟遛狗一样,干脆就叫‘小狗子’吧。”朋友的儿子上初中,期末考试没考好,家里鸡飞狗跳,朋友来找她诉苦。她反而开导起对方:“学习不好又怎么样,不配活着吗?再说又不是不努力,已经尽力了呀。如果像我儿子这样,你们怎么办?”认识自己星星生病后,张洁从没停止过学习、观察儿子的行为方式,也重新认识了自己。自闭症人有一类典型症状,叫刻板行为。比如带星星出门散步,必须走规定的路线,如果换条路走,他就大哭大闹。实际上,这是他理解世界的规律:从地点A到地点B,要通过路线C,这是一套完整的秩序。一旦秩序被打破,他就会很焦虑。张洁联想到自己,职称就是她工作中的秩序。她对工作早已感到厌倦,为了评职称,写不完的论文,填不完的表格,她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,只是被环境裹挟着,在评职称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星星的自闭症,打破了她的秩序,让她按下暂停键。请假带星星干预期间,她重新捡起了年轻时的爱好——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史。这一看就陷进去了,她找到了自己真正想教的内容。回学校后,她迫不及待申请开一门选修课。为了开课,她趁儿子去机构或入睡后的间隙,手打了12万字的教案。带孩子干预的职责变成夫妻两人分担,上午丈夫带,下午张洁带,家里还请了特教。她也会教,不过教得很“佛系”,都是一些最简单的指令,“跟妈妈亲亲”,星星很快就学会了,仰起头跟她碰一碰嘴。她觉得儿子还是喜欢自己的。闲下来的时候,她在知乎上回答关于自闭症家庭的育儿问题。在一个回答里,她写道:“很多自闭症妈妈不快乐,是因为太想做一个好妈妈了。”有同为自闭症患儿母亲的网友给她发私信,说自己特别后悔当初没有辞职,耽误了孩子的干预。现在怎么教都不会,感觉对孩子的爱意正在慢慢消失,继而自责,强打起精神努力训练,很快又受挫,陷入恶性循环。相似的经历戳中了张洁。她想,是谁规定的,妈妈就一定要无限包容、无限热爱自己的孩子,一定要无限牺牲自己、成全孩子呢?“在做好一个妈妈之前,先做个人吧。”她给这位妈妈的建议是,多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ibhjw.com/kjsczl/13593.html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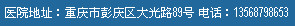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